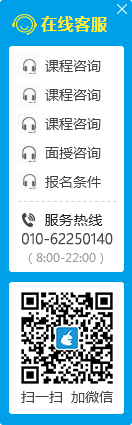所谓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消息。但这一定义,乃是基于事后的判断,传播谣言者大多是不知真假或不具备判别真假能力者。因此,自古以来谣言无所不在。在网络环境下,谣言更是“如虎添翼”,不需要口口相传,而是数字化生存。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包含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传播速度和广度加倍。借助网络手段和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谣言的散布和传播几乎独角兽司法考试网是同步的。二是,受众会迅速参与传播,并呈几何倍数增加。在自媒体环境下,微博用户有能力在几分钟内传播上万次谣言,并在同一过程中不断增加一些虚构的情节。三是,貌似强大的外表下,也有“脆弱”的一面。网络谣言往往极为短命,上午的谣言下午即消解并不罕见。谣言愚弄了网民的智商和情感,最终会遭到网络社会的唾弃。
客观地讲,即使是在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度,也不允许谣言横行。谣言可能荒谬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对个人、对商誉造成极大的损害;谣言可能煽起误解甚至仇恨,引起混乱而危害社会。刑事法律需要为治理网络谣言做些什么?在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相对健全成熟的国家,对于网络谣言的控制目标也仅仅局限在涉及“诽谤”、“名誉”以及“公共安全”等传统科目上。我国刑法上关于网络谣言入罪的条文,主要规定于第246条的诽谤罪和第221条的侵犯商誉罪。当然,个别内容特殊、后果严重的谣言还可适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罪名。
对谣言不加管制是危险的,但对谣言的过度打击,却是更加危险的。对于网络谣言的界定同样如此。因为谣言本身的特点,任何人在事先都无法确认某一条消息的真假。人们传播谣言,其本质是因为他们在传播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况且,相对于传统媒体,自媒体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经常充斥各类不真实、不充分的信息,人们识破谣言的机会和能力大大降低。所以,严厉打击网络谣言传播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同时,从证据法的角度,亦很难在事后认定谣言传播者所造成的后果。换句话说,从谣言传播者的主观上而言,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所传递的信息是谣言,更不能预见到这个信息可能造成的结果。如果行为人将虚假事实误认为是真实事实加以扩散,绝无承担法律后果的必要。
以诽谤罪为例,在网络谣言可能构成的诽谤行为上,笔者认为,证明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主观故意。通说认为诽谤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并具有贬低、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这也应用于网络谣言形成的诽谤。诽谤罪的故意是否只限于直接故意?有人认为,可以包括间接故意。因为造谣者对自己帖子的影响力是不能确定的。对此观点,笔者难以认同。因为网络影响力的不确定性,传播过程的角色模糊性,无论是发帖者还是组织者都很可能难以控制事件的发展,对犯罪主观方面的把握才必须更加严格,否则可能误伤舆论。
第二,情节严重。有人指出,网络传播谣言本身就是情节严重的表现,因为影响者众,微博转发动辄以十万计,这和传统的诽谤相比,情节绝对严重(损害商誉罪的司法解释即持此观点)。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互联网信息飞速更新,人们关注度持久性差的特点。虽然造谣者在网络上独角兽司法考试网铺天盖地散布对他人不利的言论,但受众的关注点是短暂的,并且自媒体天生的“自我纠错”功能也能起到抵消效果。所以,执法部门不能单从传播方式和效果方面考量情节,只有当侵犯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的重大损失,才可启动刑事手段。以新乡市某高级中学校长刘某被微博抹黑一案看,围观者虽众,但几乎都不相信谣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网民的识别能力在提高。本案因不存在人身、财产损失,就不能算情节严重。
第三,区别对待。谣言滋扰的个人,可以分成两类,普通人和公众人物。对于公众人物的刑法保护应该有所节制,在诉讼法上,应从证明程度上加大难度,体现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司法实践中,已经体现出这一审慎态度。2010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指出,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这些规定都表明,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是公众人物,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诽谤案件,在证据规格和定罪标准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涉及到针对公众人物,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谣言”时,即使有不实言论,追究也应慎重。如果不能证明网络上的谣言行为、抹黑行为出于对方的蓄意造假,那就应当推定该抹黑是正当的批评和善意的监督。
对网络谣言不加治理是危险的,但轻易动用刑法,甚至侵害到其他言论的自由,却是更加危险的。所以,在判断是否对造谣、传谣者启动刑事手段时,我们必须审慎考虑其主观动机、造成的实际损害以及使用证据证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