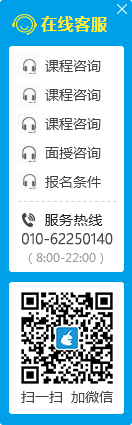实证研究方法在法学界兴起之后,域外经验和模式被迅速介绍到我国,其中,以美国维拉司法研究所为代表的以促成司法制度改革为目的,设计试点进行评估、推广的实验式实证研究模式被学界普遍认为与我国原有的“试点”模式天然契合,又在方法上弥补了我国旧有模式的不足,因此受到了学界的普遍推崇。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鲜有严格按照维拉模式推行的试点。独角兽司法考试网的老师认为,维拉模式与我国司法改革试点模式之间的某些显著差异是造成这种“叫好不叫座”现象的主要原因。
■主体立场不同
维拉研究所作为一个私立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在研究立场和资金来源方面完全独立。他们通过细致的前期调查发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需要,然后吸引有兴趣采取行动的政府机构配合参与,出具概念性报告说明改革构想,据此设计试点进行评估,说服决策者接受并推广试点方案,相当于是专门为司法实务部门设计、制作并向其推销某种“制度产品”,整个过程是开放性的、市场化的、可竞争的。在试点过程中虽然有司法实务部门的协助配合,但其与司法实务部门之间相互独立。
我国的司法改革长久以来都实行司法体系内部的自我改革模式,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是在司法体系内部进行,由司法机关主导。民间机构、学术团体除了依附于司法体系之外并没有像维拉研究所一样以制度产品提供者身份独立影响司法改革的渠道。近年来学者对司法试点的积极介入虽然给试点的具体操作增加了理论色彩和技术含量,但依赖实务部门支持的学者很难保持完全独立的研究立场。司法机关成为司法试点的积极推行者,这是我国现有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对司法改革的经验积累意义不容否认,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难以避免司法机关自身与实验结果产生利益关联,出现一些学者所言的“司法改革的形式主义和盲动主义”倾向。一些实务部门出于追求政绩的目的启动和主导试点,往往既是实验主体又是实验对象,既设计又评估,对结果的功利主义倾向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试点的实际效果。
■效果评价标准不同
在维拉模式下,决策者是否接受维拉的制度“产品”基本上取决于项目的实用价值和社会效果,即他们具体的设计方案、评估论证模式是否合理有效。维拉研究所不仅要设计详细的制度操作方案,还要提供详实的效果评估报告,以说服决策当局采纳他们的方案。维拉司法研究所药物使用与精神健康项目主任吉姆·帕森斯(Jim Parsons )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强调了评估是试点的重要内容,使用有说服力的方法异常重要。在他撰写的详细介绍维拉模式的《试点与改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一书中还特别谈到,评估结果时要承认局限性,保持审慎,因为在更长时间段内随着采集数据的增加,早期的评估结果通常会发生变化,优秀的评估者会努力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可见,维拉模式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试点效果评估标准(独角兽司法考试网整编)。
反观我国,具有公信力的试点效果评估标准尚未形成。报纸所见常常是“某某试点效果明显”的报道,期刊所见也往往是没有客观评估标准参照的“王婆卖瓜”式的实验报告,大量篇幅用来阐述试点的正面效果和可行价值,而对逻辑论证和结论的适用条件、范围和局限性着墨甚少。极少有承认试点不符合预期或假说不成立,并坦然以失败的实验为样本从中提炼道理、总结经验的案例。有的试点前期宣传大张旗鼓,后期效果不够理想,就迅速销声匿迹,具体原因和数据却语焉不详或不肯公开。与之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不但预设了立场,而且对实验过程、条件、数据、结果都进行了人为控制的“伪试点实验”,徒具“实证研究”外壳,却能以预设结果博得皆大欢喜。规范的试点效果评估标准的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无效试点的反复启动和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功能定位不同
维拉的试点模式使用的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方法,讲求以严谨的态度、中立的立场、严格的程序、科学的方法和令人信服的评估标准推出高质量的司法制度产品。这种路径秉承由经验推出理性、以数据对比讲道理的原则,有很强的研究性,同时也非常注重实用性,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设计服务,甚至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其几乎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只接受决策主体基于实效性的选择。
我国的司法改革试点所承载的功能则有所不同。有学者直言,自近现代以来,从中国司法的最早变革开始,法治和司法不但一直是政治的引导和塑造,甚至其发生就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政治回应。目前的某些司法改革试点未必是单纯地从实际需求出发,有时也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附和与回应,因此其功能和价值评价也必然有异于维拉的纯粹实证标准。
由上述差异可见,我国要想如一些学者所言以维拉模式为范本进行试点改革还要跨越较多的障碍。其实,我国能否全面照搬维拉模式都不会影响司法改革的进程,但两种模式对比之后折射出的我国司法试点中的问题却不容忽视。我国只有树立客观的司法政绩观,建立科学的司法业绩考评制度和司法官员升迁制度,引入社会力量和民间力量参与和评价司法改革试点机制,才能将司法试点的真正目的还原为针对现实需要的有益尝试,才能强化司法试点主体的客观立场,使试点更具公信力。